中国现代诗歌自1915年胡适提出“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以来,开始了它跌跌撞撞的成长历程。那时的它,宛为一颗胚胎,茫然地蜷缩在缺少氧气的海洋里。
它虽茫然,但时间没有辜负它的等待。
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杂志为新诗首发其声;1920年,胡适的《尝试集》成为白话新诗的最初探索,颂出自由与民主,这一著作的发表,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革旧迎新”,诗歌从此开始了新的纪元与生命。当时以胡适为代表的诗人们认为旧体诗的刻板与顽固阻碍了自由诗歌内容的发展,刘半农、沈尹默、俞平伯、康白情等人紧接着也唱出初期的白话歌声。而后,“五四”白话新诗运动成为中国诗歌发展的新纪元。此时外国诗歌对中国新诗有着十分巨大的影响。到了20年代,以“新月派”为首的诗人们最先向“白话诗”发起了进攻,认为“白话诗”没有纯正诗歌的美的传统,“白话诗”虽新,但“新”得丢失去了诗歌体式本来有的规范和格律。闻一多也写出了“三美”之论,在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这三个角度对新诗进行了规整,也是对着早期如外国诗的“白话诗”作了反击与纠正,在扭转“非诗化”的倾向上作出了努力,企图让大家的眼光能够重返诗的本质,爱诗本身的美。此时,“新月派”为首诗人徐志摩渐生出一些佳作,其浪漫多情的诗歌风格,充满想象力与鉴赏力的语言,使其成为中国新诗的一位代表作众多的优秀诗人。在那康桥的湖畔,诗人满怀着依恋望着母校的一草一木、一花一树,吟出歌声的挽谣。
意识到这点的中国新诗界,开始将注意转移到自由诗与诗的散文化之上。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诗人是戴望舒,他的《雨巷》唱出纯粹的“诗情”,流露的真情实感让许多人为之动容。《望舒诗论》的发表,阐述了他对于那些过于纠结诗歌体裁与格律导致过往矫正的错误的反对,诗歌只应该是颂情达意的抒发,太过于集中平仄和韵脚反而累赘。更有甚多他对于诗歌的独特理解和创诗时的一些历程与感受。这一著作对后来中国新诗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另有艾青提出“诗的散文化”的主张,以此来保护诗歌的自由与徜徉。“散文化”良好地避免了胡适所言“作诗如作文”中“文”这一次的浅薄,又不执着于近似“古诗”导致的刻板。确如所言:“自然的终点便是艺术的起点”,“只有不会跳舞的才怪脚镣碍事, 只有不会做诗的才感觉得格律的束缚”。借着“散文”文体的自由与美感,提供了诗的未来,为诗歌的发展创造了十分充裕的空间。卞之琳、何其芳等人也发表自己对于诗歌格律的看法,对新格律诗十分推崇,同时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且艺术造诣很高的作品。卞之琳的《断章》更是当时诸多诗作中的佼佼者,寥寥数句,尽数哲思,时间与空间的转换,人与物的情对,更有未言尽的空间之内的其他画面,让人遐思与揣摩。随着诸多诗人的诗的创造与贡献,新诗的发展渐渐走向了正规,这路程中诞生了许多璀璨的明珠。
但未等得及新诗平稳长大,战争来了。家国的破碎,生灵的涂炭,使诗人们放下了一切自我之歌。此时的诗大都为了被流放的土地、被欺虐的人民、悲惨的家国而唱,他们悲叹、愤怒、压抑、迷惘。闻一多所作《七子之歌》、艾青的《我爱这土地》莫不都说出了家国灾难下,心中对侵略者的愤恨、对祖国的深爱与痛惜。这时候的诗人们不再只关注艺术;不再只坚守自我的小天地;不再无病呻吟,心中最底的愤被点燃,最深的那一抹爱被激发。于是,催生出许多时代的高歌,激励着爱国的情怀,抗战时期的诗歌也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由今看来,历史的尘嚣不应被遗忘,应永远铭记于心。也更让人意识到:文学创作者不应只在文学圈中里埋头创作,也应随时代而行,将情感融入到民族与国家中去。同时可见,社会的动荡也成为新诗发展的重要因素。
往前看,中国现代诗歌在文化追源上是复杂的。它与世界诗潮有着密切联系;虽迫切想冲破传统的羁绊,但无法割断中华千年的传统诗歌文化,并在某种程度上,传统的文情对现代诗人的创作产生深层次的影响。更重要的原因是根基问题:新诗在挣脱羁绊之时,没有了传统精神的支撑,便无法保证其自身的价值及其发展,传统诗歌中的意境、意蕴以及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精神是新诗创造的丰富土壤。正因如此,中国现代诗歌融古通外,逆向传统是创造,欧化亦是当时的必经之路。中国现代诗歌在创新与继承中坚定地往前走着,其中诸多不易,却也生出了许多动人的果实。
回望这百年新诗,在建立的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与磨难是当下的我们无法体会的,那些诗的先驱者们,排除的障碍与艰难又何能用一言二语道清。诗歌那颗弱小的胚胎,不止有亲生哺乳的母亲,更有漂洋过海而来的养母,它从中汲取的养分、它自身的亦步亦趋与小心试探、它努力克服着自身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都是它成长过程的必经之路,虽然颇为艰辛。中国新诗就像那潺潺的流水,遇难则波涛汹涌,虽水路遄急,方向时而会错,但它都在冲击的过程中前进,在曲折的道路上上升,又在平缓之处涓涓细流,发挥着自己的光和热。在这条水上,渡过安稳的小船,浇灌沿途的花朵,给予鱼虾栖息之处。也让多年后的我们感到一丝清凉与慰藉,更多的是那一份感动。这些诗人中更有“诗国的哲人”,他们大都以诗的哲思闻名,造诣独特,引人深思。以笔者浅薄的阅历和审美经验,在阅读中国现代新诗的过程中,隔了百年,字里行间,也能感触到前人们创诗时的真切实情:或是个人情的流露、或是对沉沦母国的呐喊、或是个人心灵的救赎、或是只诚实爱着美好。这一些都像繁星点点,缀满深邃的天空。
是否可以这样想:诗歌是文学永远的灵魂,诗人创作的一字一句莫不都是他们灵魂的低吟,诗人打破习惯将习以为常编织成陌生的谣,但却唱出最深处的灵动之歌,这时,诗人给我们的,也正是我们给自己的。
佛曰:众生是佛。诗也在你我的心中。(蔡林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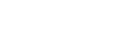





 甘公网安备 62010502000334号
甘公网安备 62010502000334号